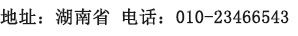本文已刊于《宝安文学》,现全文一次贴出,并附图
回裤裆湫
从沙井到佛山西
我在深圳生活了近三十年,这次回到故乡才知道,小平故里有个广安(深圳)产业园,简称深广产业园,亦称深圳“第十二区”。以我有限的认知,深圳本土目前有十个区,那深圳“第十一区”应是深汕合作区。而深圳把“第十二区”设在四川广安,或者说广安能争取到深圳多家大企业前来投资,自然与“小平故里”这一概念有关。我们都知道,从某个角度讲,没有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或许就没有深圳今天的繁华,更没有广安目前所呈现出来的景象。
那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呢?我只能从我自身的经历说起。
历史不可假设,个体命运也一样。在故乡广安,我有两个家,一个是我的出生地裤裆湫,今属广安市前锋区,已破败多年;一个是我女儿们的出生地火山村,位于广安区枣山物流园,紧临协兴园区,现已拆除。
火山村的房子是旧历年二月被推掉的,离我正月初六重返深圳上班刚好一个月,那个春节便成了我在火山村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拆迁协议春节前就签了,因拆迁户太多,岳父担心到时租不到划算的房子,签完协议就去镇上老街租了一处极其便宜的旧房子,余下一大半过渡安置费,说是用来买米全家人可以吃一年了。我和妻子都希望他们租住在小区里,毕竟孩子们一天天大了,安全和卫生应尽量讲究,却未能说服他。他说田没了土没了,一家人到了镇上吃一口水都要钱,得划算着用,又说,怎么样也比农村好呀,茅草棚棚我们还睡了几十年呢,这高楼大瓦的风吹不垮雨淋不湿有啥不好啊?
当时,还有好几户人家未与拆迁队达成协议,成了所谓的钉子户。我们家算签得比较早的。那房子是年盖的,当时钱不够,就两层,未装修,后来想盖高一层再装修一下,上头又不允许了,说是在红线范围内,枣山全域已被规划。房子朝南,屋前有晒场、菜园、柚林、鱼塘和庄稼,屋后是一片荒地,可养鸡鸭和牲口,我们坐在堂屋里就能看到广安城一天比一天大,直到把整个火山村都吞了。
小女儿快上学前班了,住镇上方便,加之那房子盖得便宜,扣除安置房面积还能余几个钱,岳父在签协议这事儿上没讲多话。
房子是拆了,地却未征用,说是租借给建筑公司堆碴土。广安地区紧临重庆,除了山区便是丘陵,城市沿渠江而建,近年主要向西南方向延展,无论建楼还是筑路碴土都特别多,把地租给人家当碴土场似乎成了一门不错的生意,许多偏远的山沟沟都这么干。近年来,任何一座城镇都能找到大兴土木的理由,可谓圈地成风。据说那火山村四周已被医疗集团、教育集团和房地产公司征用。再往镇上去,诸多楼盘拔地而起,年节时,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离开土地的农民和务工归家的民工在小区门前跳着舞摆着摊儿扯着圈子,城市气息扑面而来。
医院已征用村里部分土地,一些60岁以上老人买了社保并转为城镇居民。每年社保到账后,村里所有60岁以上的老人平分,似乎也挺公平。岳父岳母均年过60,据他们讲,社保费、过渡费、土地租金等到手后,如果省一点,基本够日常零花,当然,孩子们的学杂费得靠我们在深圳打工寄回去。岳父说这话时心情是愉快的,他跟别的老人一样,觉得苦日子到头了,该享享清福了,并希望我们尽量抽空回家看看。
平时工作忙,路隔数千里,回一趟家真不容易。这些年来,我们已习惯春节回家,一到旧历冬月中旬内心就充满了期待,一有机会便紧紧盯着电脑或手机抢火车票,尽管春节假期得从除夕开始,而且仅仅7天。就算你离家再远,顶多提前三五天动身。事实上,年初出门时我们就有了回家的打算。
春节期间多雨雪霜冻,汽车不准时,路况恶劣,而机票多为全价,来回得花掉一个月工资。春运挤火车,每次行程都特漫长,总觉得这几十年来一直在火车上。广安离重庆也就一百公里左右,广州到重庆的高铁前年已开通,春运加班列车也不少,但四川是劳务输出大省,我们想买到心仪的火车票仍非易事。所谓“心仪”,一是价钱划算,二是往返日期得将就,春运抢票就成了耗时费神的苦差事和技术活。
年底,单位较为清闲,我整天木鸡一样呆在办公室,抢两张火车票并不困难。我先抢了小年后的普通列车,全程三十多个小时,后来想到妻子未坐过高铁,便希望碰碰运气换两张。深圳尚无直达重庆的高铁,而广州到重庆的高铁连站票都“见光死”,我只好换了1月29日凌晨3点从佛山西开往重庆西的高铁票。妻子却不太乐意。她说这得多花一倍的钱呀,半夜发车,头天晚上就得去佛山等,到了重庆西倒车回广安也挺麻烦。妻子在小工厂干了近二十年,前不久才去一个社区图书馆上班,活儿轻松了,工资仍不高。我的收入也有限,两人挣钱六个人花,一年忙到头稍不注意就白干了。但普客票已退,如果再把高铁票退掉,恐怕得站着回家。妻子很无奈,又想不出更好的法子。我说又不是天天坐高铁,怕啥?大不了返程时坐一百二十元的加班车嘛。
单位初七上班,返程坐慢车须三四十个小时,若能抢到初五的票最合适。凭多年抢票经验,我先抢了初四的,第二天再抢初五的。初四的票好买,初五的一点开就只剩站票了,没敢要。几天后,连初四的站票也没了。
买好正月初四返程票时,日子仍在腊月初。深圳暂无直达佛山西的火车,得去广州转。但深圳到广州南的高铁票特紧张,很难买到晚上的。坐汽车吧?沙井去佛山的车很少,时间也不将就。后来同事梁叔说他家在佛山西附近,年前想回去看看父母,到时可以捎上我们。
梁叔过两年才退休,看上去身体却不太好。我不希望他为了方便我们而开夜车,便决定请多一天假,28号下午出发,到佛山吃晚饭。
我去过佛山两次,一次是五年前去领中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奖,住在西樵山下的酒店里,第二天还去山顶见过南海观世音塑像。另一次是两年前去顺德,也是领奖,刚好碰到茨平兄。那些年茨平兄写小说和散文,多以打工生活为题材,跟我有不少共同语言,算是网上较为谈得来的文友。看上去他比我想像的年长,在一饲料厂做企业宣传,买了私家车,初次见面便一见如故。午餐后他拉着我们满佛山跑,说要找个地方喝酒。大热天的,下午三四点哪有菜馆营业?好不容易找到一快餐店,酒足饭饱后,回深圳的火车票却卖光了,于是他又把我拉到北窑去。那里有我多年不见的亲戚,说是去看看他们,其实是借宿。
那之后,我对佛山的印象更深了,总想着哪天有机会再见见茨平兄。
临行前一个星期左右,我问茨平兄离佛山西远不?回家会在那儿转车。他说就两公里,早点过来嘛。
动身的日子离正式放假还有一个星期。按单位要求,无论编内还是编外人员,提前回家或延后返工都得写请假条,超过两天扣工资。梁叔说你请什么假啊?先把年的年假休了吧。年假一休暑期就没空回去看孩子了,想来想去也只好先把年假休了。
办理好相关手续后,我开始辦着手指头期待归家的日子。妻子也为回家做足了准备,连续上一周“直落”,工作量增加一倍,很累,倒也好过以前在工厂请假扣工钱。
1月28日下午,多云,天气不错。从沙井出发,一路上除了一些小追尾事故,基本通畅。事故主要发生在广深高速上,多为国产新车。梁叔有三十多年驾龄,普通话很不标准,平时不爱讲话,一见到交通事故就摇头嘟咙几句。我坐在副驾位上,看着一堆又一堆拖家带口急着回家的人站在应急车道上不停打电话,年后去考个驾照的念头又没了。考驾照是为了买车,买了车就想开回去,说是走亲戚访友方便,可走走停停几天几夜也未必比挤火车舒服。当然,我不买车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出于经济考虑,就夫妻俩在深圳,上班用不着,又没别的业务,如果真要买,估计也得以后回到广安再买。
车到佛山狮岭时,五点不到。茨平兄说正在开会,年底老板想说的话实在太多了,还没讲完,不方便出来,先等等。我们便把车停在厂门外等。工厂大门正对着广佛城际线,铁路以西是一片荒地。夕阳正红,梁叔叉着腰,面对着夕阳下的荒草,若有所思的样子,满面挂着从未有过的深沉。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离开佛山去了深圳沙井放电影,一干就是40年,至今仍负责“送戏、送电影下乡”的工作。早些年,他攒钱盖了点小房子,孩子成家后又买了新房,八十高龄的父母不肯来深圳住,自己转眼就快退休了,就可以到处走走了,一辈子就这么平平淡淡过了。在这年末岁尾,拉着两个急于返家的四川人在老家歇脚,他的内心似乎并不比我们平静。他这次回家最多就待两天,年前还得返回深圳上班,然后春节值班,估计得正月十五后才能再次回佛山看看父母了。
门口的保安问他找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呵呵一笑,脸上充满了自豪。他说从深圳来到佛山去,我是佛山人,我在这儿耕田时你还没出生呢,问我从哪里来?真是的。
我知道,他是真的回到故乡了。据说,他的兄弟姐妹大多在深圳安家,父母仍喜欢住佛山,因为老屋还在。在沙井出发时,我见他特地去跟小弟要了钥匙,说是要回去好好看看老房子,顺便带点年货给老人们。他还告诉我,一年后就可以在沙井坐高铁直接到佛山,不用一个钟就到家了。
夕阳没入荒草时,茨平兄才笑嘻嘻出了厂门。跟两年前一样,他一边跟我谈论文学一边寻找菜馆。他说好多文友都来佛山找他玩过。他确实是一个挺好玩挺热情的人。
他说,当年老板建厂时购置了一大片土地,盖了好多宿舍,为方便职工亲友探访,后勤部留有专门的客房,已经替我们申请好了,饭后先回厂里休息,半夜再拉去火车站。我说年底你也挺忙的,干掉两瓶啤酒我们就在附近走走,半夜三更打扰你也不是个事儿。他突然笑了起来,说好吧,出门在外,这年头能见个面吃个饭就好,过夜睡觉还真不容易。
饭后我们去了他工厂对面的荒草地。进去我才发现这是个大型植物园。年底,深夜,天又冷,园内少有人走动,高大茂密的热带植物在路灯下显得很神秘。我不知道这园子究竟有多大,平时有多热闹。我们东拐西转只顾着聊天,后来竟迷了路。
好不容易从园子出来时,已近午夜。想到他第二天要上班,梁叔还得赶回家歇息,我们便直接去了佛山西站。
佛山西刚建成不久,跟我前年在广州南赶车的情况略有不同,看上去乘客并不算多,估计大部分人仍未到站候车。我和妻子接过义工免费发放的瓶装水和报纸,在二楼人少的地方找了一个避风的角落坐下。后来,我又把报纸铺地板上,用行李当枕头,让妻子躺一会儿。慢慢的,地板上坐着或躺着的人就多了。他们吃着零食玩着手机,或紧紧相拥,或由孩子敲打着疲惫的双腿。他们跟我们一样,为这次长途旅行做了长时间准备。车站里灯光明亮,地板光洁。四处张望或行色匆匆的人们在地板上留下长长短短的影子,如一幕幕旋转电影,勾勒着各自的人生,讲述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妻子在地板上躺了一会儿,说背心冰凉,得早点进候车室找个地方坐坐。
过安检后,我们才发现人们大多进了候车室,乘客并不比当年在广州南见到的少。他们或席地而坐,或撑着行李杆养神,或一边吃泡面一边看列车信息。
头班车将于凌晨两点发出,我看了看手机,凌晨一点,离我们出发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
从深圳沙井出发,已过去整整十二个小时。我站在佛山西候车室里,等待着1月29日凌晨第二趟发往重庆西的高铁。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将于十二个小时后抵达广安。这些年来,候车室里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个场景都在我脑海里烙下过印迹。在这样的等待中,我会好好想想这一年来的历程,以及来年的打算。
这种等待特别慢特别慢,慢得所有的日常生活都可以忽略不计,慢得让人感觉一生都消耗在旅途中了。
从老街到法国风情街
上车后,窗外仍黑洞洞的。妻子第一次坐高铁,并未表现得特别兴奋。她在亲友群里发了两张照片,说上车了,最快中午可到广安南站,谁来接我们?
广安南坐落于枣山园区,离我们的租房不过两公里,公交车七八分钟,如果行李不多,步行也没啥问题。亲友们大都买了私家车,岳父有一辆三轮电动车。如果天气好,都是岳父年末接我们回家,年初送我们出门。这次我们特地交待了,让他在家等着,天冷,出门风大,别再操这份心了。岳父患气管炎多年,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冬天一吹风就会感冒,特别难受。
车入贵州境内,天微明,群里有人回信息,说都在二叔家团年呢,你们到了重庆再说吧,谁接都行。二叔是妻子的二叔,属广门镇,家离车站也不远,前几年盖的新楼,未拆迁,团年饭仍在乡下办。其他租房的亲友住处窄逼,团年时得去饭店包席,有的三五桌,有的七八桌,能叫上的都叫上,说是过年人越多越旺。
我们以为岳父带着孩子们去了二叔家团年,在重庆西下车后,并未告知他。重庆西较为偏远,运营不久,即便春运发往周边的班车也不多。广安境内原本有好几个火车站,仅襄渝线上的前锋站车次较多,但离广安城区好几十公里,很不方便。而广安南站位于南充到重庆的一条支线上,平时除了几趟去成都的动车,与重庆之间并无往来。春运时,重庆北到广安南加开了三趟临客,其中一趟中午一点从重庆北发出,提前4天放票,结果我们连一张站票也没抢到,只好买了12点由重庆西开往广安客运中心的汽车票。
好在并未下雨,也没起雾,车到广安时不过两点半。来接我们的是二叔的儿子阿全。他前些年在贵阳搞装修,算个小工头。后来孩子大了得在老家上学,又听说家里到处是楼盘,他便把队伍拉回广安,从一个大装修公司接些小活。回广安前,他把先前的破长安车卖了,另买了一部稍好的二手长安,说是面包车实用,拉人拉货都行。
他看上去有段时间没干过体力活了,胖了,烟也不抽了,对客运中心周边的路况不太熟悉,被交警赶来赶去好几次才找到上客点,也不知被抄牌没有。
坐在阿全那被装修材料整得破破烂烂的二手长安车里,故乡的天空变得灰暗了起来。出客运中心不久便上了迎宾大道。迎宾大道西接枣山高速出口,东至城南五福桥,路两边被绿色屏障遮得严严实实。那些高出屏障的树冠上已挂满彩灯,大红灯笼在灯杆上迎风飘荡,空气中散发着新年的气息。
出迎宾大道左拐时,我发现故乡的很多道路跟深圳的一样,侧边绿化带和人行道已被挖掘机掀开,裸露出新旧不一的土石和水泥块。我们的租房位于枣山老街。老街上破旧的店铺门口摆放着各种应节礼品,除了包装华丽的饮料和五花八门的食用油,也有许多传统年货。街面坑坑洼洼的,两旁停着许多外地牌照的小车,有新有旧,档次不一。上了年纪的乡下人仍未来得及换上节日新装,肩挑背扛挤在店门口讨价还价,企图用丰富的物质来回馈一整年的辛勤和付出。
车欲拐进租房小巷时,我听到了一阵阵悲怆的唢呐声和密集的鞭炮声,闻到了火纸燃烧的气味儿。
又死人了,在行大礼,车进不去了,都快过年了还敲敲打打的,真是的!阿全说。
是啊,快过年了,我说。
车确实进不去了,即便能进去估计他也不会开进去。所谓行大礼,就是老人过世后出殡的头天下午举行的最为隆重的法事。而巷口右侧正好是一家棺材铺,就算不遇到这件事,亲友们的车一般也不会进巷子,能绕开棺材铺都会尽量避开,何况是年末岁尾。
这棺材铺有好些年头了。铺头临街处搭了个木棚子。白天,上过黑漆的棺材就摆在巷子里,棚子里则是些半成品或刚成型等着上漆的白棺材。据岳父讲,时下做棺材多为机械加工,轮廓清晰,线条流畅,里内光滑,尺寸标准,样份好看,但材质大不如从前,多为水柏或椿树,不中用。他还举过一个例子,说上次奶奶迁坟时,村里有些新坟尚不足两年,水一泡那棺木就朽掉了。奶奶的棺材是旧时请木匠来家里制作的,硬柏木,虽然比人家的先入土一年,却几近完好,因为材质好,经得起水泡。
这年前过世的老人是谁呢?阿全也不清楚。到家一打听,得知是隔壁楼房东的母亲,90多岁了。老人儿孙满堂,腊月初就走了,后人们为择得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吉日,遗体已在家里整整放了三个星期。经过近几年发展与扩张,这枣山老街已被重重高楼包围,像个孤岛,按深圳的说法就一城中村。年末,政府已出文件,城区全域禁放烟花爆竹。所以,来宾或法事上的爆竹点燃后全被丢进了门口大铁桶里,烧钱化纸也有固定地点,不像乡下那么随意。
岳父见我提起这些事,又举了前年一事例。他说,前年村子里唐老婆子去世了,在家里放四十多天,好折磨人哦,以后我走了,当天就拉去烧了,灰都莫留一把。妻子说灰还是要的,甯家沟不是有公墓吗?又不贵。岳父常年多病,吃过很多苦头,早已看淡身后事。他常常会不分时间和地点安排着后事,一再要求从简。他说村子被推了,那些土葬埋大料(传统棺材)的,买地皮要钱,跟甯家沟的村民商量还要请吃请喝,埋个土堆堆两三万块,有啥意思?不如一把火烧了去馆子里搓两顿。后来他又说到了爷爷和奶奶,说爷爷去世五十年了,敞坟时就剩两条大腿骨,旁边那些无名坟敞开后,头骨被人东一锄头打过去西一铁锹铲过来,从坡上滚到水田里,鬼都不晓得。最后他还说,你奶奶入土才三四年,开棺后就剩一把骨头,用袋子一笼,提在手里哗哗地响,她听到吗?人死如灯灭。
岳父每次聊起这个话题就特别来劲儿。他并非绝对的无神论者,只是对身后事不以为然,说到底也就为了省钱省事,尽量不给后人添麻烦。他说奶奶在他十三岁时就守寡了,居然活到了八十多岁,作为长兄,他把二叔和三叔拉扯大,还帮他们立了门家户,现在孙女都读高中了,啥事没经历过?算命的说他活不过54岁,结果快70了还是老样子。我们清楚,他这么说的意思是让我们平常也注意节省,存点钱,别到年老时受穷。
租房在顶楼,两通,上面盖了青瓦和隔热板。临街的窗子挺大,光线不错。整栋楼就三层,预制结构,地板没铺砖,脚步重了都起灰尘,是老街建得较早的楼房。大女儿和老人们的床铺之间扯了一条布帘子,好在她住学校,少回家,平常回来还可以睡我们的床。我们的床是用两条板凳和一张木板搭成的,搁在另一通靠窗的地方,我们不在家时就空着。床前的窗子太大,岳母便用一块粉红色长布一遮,倒有了些喜庆的色彩。
我点燃一支烟,趴窗台上朝下看。巷子上空扯了半透明的雨布,伙计们已摆开桌子,铺上白色桌布置好碗筷,倒酒的倒酒,炒菜的炒菜。热气腾腾的蒸笼下烈焰滚滚,纸钱味、扣肉味夹杂着锣鼓声、唢呐声和鞭炮声,在腊月二十四的老街夜空回荡。我知道,这里是四川广安,小平故里,具体一点是一个小镇上的一条老街,或者说一个城中村的某条巷子里。旧历年末,这些跟泥土和庄稼打了一辈子或者半辈子的人,离开村庄来到这里,正在为一位出生在上世纪初叶的老人超度。她的子子孙孙、生前好友、四邻五舍正从全国各地回到故乡,以告别的名义聚在一起喝酒打牌,询长问短。这是一场发生在我们楼下却跟我们完全无关的葬礼。岳父在此住了一年,几乎认识老街上每一个生意人,似乎跟谁都熟悉,但因平常不曾往来,镇上一般人家的红白喜事都不会去随礼吃酒。房子拆掉后,并非整个火山村的人都住到了老街,有的去了稍远的乡下亲戚家,有的在城南或城北买了住房,虽各散五方,但谁家摆酒大伙儿还是会去凑个热闹的。
故乡的酒席大多兴在腊月末或正月初,以便出门归来的人聚会。广安人好热闹,爱摆酒,礼金元起步。这元会全部花在酒席上的,绝不是为摆酒而摆酒。即便是乡下的坝坝席,你吃过也一定会觉得特别丰盛。如果你因工作太忙送了礼而没去吃酒,主人家会不高兴的,下次在酒桌上见了面还会提起并责怪你几句。广安人好客,家里来客人了,小孩会发“客来疯”,兴奋得故意犯错,知道大人不会当着客人的面责骂他,而客人走后他们的气也消了。
岳父经常说起的话题便是老家的酒席,然后就说说一年来的开销。孩子们的学杂费生活费,一年请了几次客,送出多少礼,买了什么大件物品,住了几回院,房租多少,油盐米醋气水电等日常开支多少,都清清楚楚。妻子跟父亲对着全年的收支,挺认真的样子。我不爱管家务,也不管钱,甩手掌柜一样坐床上,一边抽烟一边打量屋子。这屋子实在太简陋太旧了,一住就得三五年。我觉得老人们越来越老,孩子们越来越大,应该找一处较好的房子。我试着说出心里的想法,却被他们反对了。理由很简单,说到时候安置房分下来,装修要钱,孩子们上学要钱,没田没地的,能省一个是一个。
之后我就不怎么说话了,一是觉得没什么好说的,二是赶火车几乎整夜未合眼,实在困。阿全不抽烟了,话也少了。他大概说了一下目前广安的发展形式和来年打算,信心满满的样子。最后他说到了团年饭,说一家老小为了等我们回家都没去他家团年,记得改天一起去吃一餐。
阿全离开后,岳母端出地瓜粥,切好香肠腊肉,问我们午饭怎么打发的?我说四五十岁的人了,又不是头一次坐火车,不会亏待自己,你们就别操心这些了。
大女儿在城南补习功课,到家时已近傍晚。小女儿四岁半,已上两年幼儿园,个头高了不少,先前跟我们视频时特别调皮,见了面却自顾自看电视,反倒生疏了。
晚饭后妻子翻出零食和新衣服,小女儿判若两人,爸爸妈妈叫个不停,还从书包里翻出作业本和奖状讨好卖乖。我抬头望了一眼竹杆上的腊味,比往年少了。岳母说年前闹猪瘟肉特别贵,没准备多少,屋子太小,团年饭和正月间请客都得去馆子里,到时全部背去深圳都行。我说深圳天气热腊肉吃多了上火,正在减肥,可以少带点。
楼下正办着丧事,特别闹,我只好关紧门窗。腊味挂在我的床前面,孩子们在隔壁围着电视跟大人们有说有笑。听着他们的笑声,闻着床前的腊味,我才觉得真的快过年了。
这时电话响了。从东莞回来的一高中同学组织饭局,要我立即赶去城南西溪河边吃扒骨肉啃猪啼。我说吃过晚饭了,坐车好累,能不能改天啊?他说有好几个是毕业后第一次见面呢,你自己看着办吧。
想想,还是去吧,毕竟好些人快三十年没见过了。
同学见面,免不了话旧,喝酒。一喝就是夜里十点过。酒后大伙儿都不敢开车,好在那地儿离住处不远,叫个滴滴才9块钱。
一路上我就想,住城里确实好啊,喝再晚都能回家。
到家时他们已入睡。我闭眼倒在床上,听着楼下的唢呐声,好不容易才迷迷糊糊睡去。
岳父叫醒我们时天还黑着。我看了看手机,凌晨两点过。岳父说楼下要“背电”(闭棺准备出殡),得把睡着的人叫醒,不然会被带去阴间。全家老小都被他叫醒了。孩子们特别听话,似乎明白“背电”是怎么回事,都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岳父趴窗台上,等棺材被人抬到巷子里才叫大家继续睡觉。
楼下仍闹哄哄的。我有早醒的习惯,这么一折腾实在难以再睡。我想起白天在车里看到的街景,想起跟妻子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老街综合市场上。那年妻子才十九岁,见面后我就去了她火山村的家里吃午饭。当时他们家还在磨盘山坎上,两间半草屋,一条小土路,步行得一个多小时。转眼十八年过去了,大女儿上高中了,草屋变成了五通楼房后来又被推掉了。据说在老屋附近小平大道与火山大道交汇处已立起一百多个塔吊,十余个楼盘正如火如荼地平地、打桩,其中一个开发商竟是我的高中同学。
高中同学中有经商的,从政的,教书的,也有从外地回来建厂的,都比我这个在深圳生活了快三十年的打工仔有出息。同学们见了面,直呼姓名,谈天说地,毫无身份地位贫富之分,又那么的融洽。我是一个不善交流的人,私下加